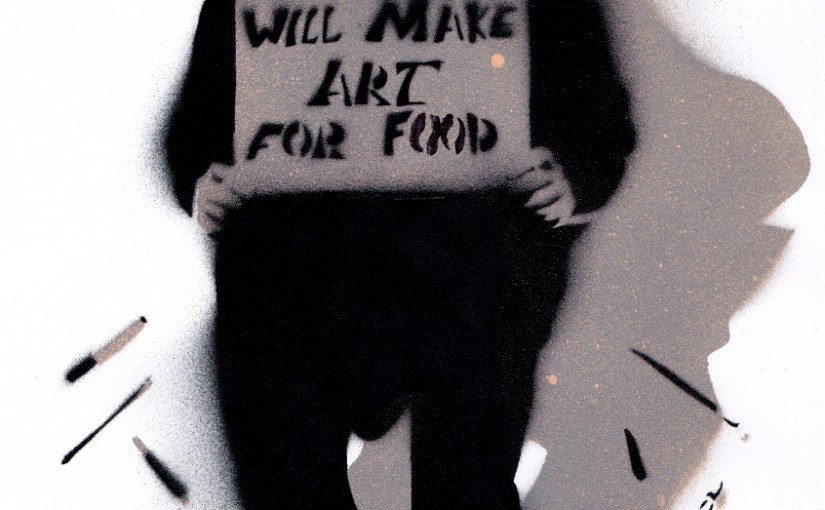海倫自稱是一位來自德國的藝術家,約五十歲,是我多倫多的室友。
海倫自稱是一位來自德國的藝術家,約五十歲,是我多倫多的室友。
去年九月份,經另一位藝術家朋友的介紹,我住進了海倫租住的房子。那是市中心的一幢三層樓的房子,看似高大,實佔地面積甚小。這房子位於較貧瘠的葡萄牙人社區,被密密匝匝緊挨著的雙層連體樓(Townhouse)左右擠兌著,就如夾心餅乾之夾層奶酪,經左右一捏,奶酪就變型長高了。房子的一層為另一住戶,分門進出,與我們無相干。二層有兩個房間,海倫住一間,把另一間二次轉租給我,我們共用廚房廁所。三層是海倫的藝術工作室,聼說她做些紡織類的現代藝術作品,但很少賣得出去。
海倫個子高大硬朗,約有六英尺高,這是第一印象。她的單車既高又黑且重,非婀娜女性之款式。海倫臉部肌肉也頗硬朗,歲月的皺紋勾勒出各部分肌肉的素描輪廓。此臉在不作聲時是很莊嚴的,有如一尊青銅鑄成的沉思者塑像。海倫在公園兼職當保安人员,她的身材及臉部表情有明顯的工作優勢。據她自述,公園裡總有一群吸毒之不良少年幹壞事,警察非大事不干預,每每是她責無旁貸把他們唬住嚇跑。此我信也,我雖年輕力壯,但若與之過招,卻難免三兩回合就四肢撲地。我隱隱約約覺得西方女權主義之厲害。
海倫大大咧咧,不拘小節。這是第一個月裡我對她的了解。她從不計較我按自己喜好搬弄廚房廁所的擺設,不介意我的畫掛在她房門附近的牆上。需要她幫忙擔擡重物上樓,她也爽快利落。她說話直截了当,從不含糊。她少用修飾的形容詞,多用直來直往的動詞,請求時少用疑問句,而多用祈使句。“明天你必需把錢給我。”海倫對每月都準時交房租的我說的這句話顯得多餘和粗魯,尤其是在注重謙讓內殮、言必有“請”字的加拿大。但我並不在意,知她只是直心直口而已。海倫飲食粗獷,早晨起來端出一大鍋,將小麥類、蔬果類、奶酪類及肉類食物不分青紅皂白同時掉入鍋中,用大勻攪和後端起就吃,吃剩的部分就是晚餐。海倫極少塗脂抹粉,她的衣服盡是耐磨的粗棉布料,式樣怪誕,多純色,調偏暗。有時候,她在額頭上系一白色帶花的繃帶狀綢緞作裝飾,綢緞另一頭長長垂及腰間,既象是街头抗议示威者,又象活脫的巾幗英雄。她還把又 長又厚襪子套在緊身的褲腿外面,這種衣著習慣異常,在多倫多少有同類。我戲稱之為巴伐利亞藍領時尚。有一回,我的文質彬彬的Timberland書包拉鍊壞了。我找她幫忙縫補。拿回來一看,書包成為一個針線雜亂無章,慘不忍睹的怪物。始知海倫絕非淑女,且略知其藝術事業不暢之由。海倫倒也率直,稱自己手工實在不佳,甚為抱歉。
長又厚襪子套在緊身的褲腿外面,這種衣著習慣異常,在多倫多少有同類。我戲稱之為巴伐利亞藍領時尚。有一回,我的文質彬彬的Timberland書包拉鍊壞了。我找她幫忙縫補。拿回來一看,書包成為一個針線雜亂無章,慘不忍睹的怪物。始知海倫絕非淑女,且略知其藝術事業不暢之由。海倫倒也率直,稱自己手工實在不佳,甚為抱歉。
漸漸地,我發現海倫的粗獷有過份之處。家裡衛生她少在意,飯後從不洗碗,地髒了視而不見,她甚至會忘記沖廁所。這苦了我這小男人室友:經常洗碗掃地,間或還要掩鼻沖廁。如此置生活細節於不顧之二十一世紀藝術家女性,實為罕見。海倫還有特殊習慣:她每天都把食物垃圾置入塑料袋放入冰箱的冷凍室,理由是防止食物垃圾在垃圾桶內變味滋生細菌。因為她每週僅清理一次垃圾桶,所以此舉似乎必要。不過,冰箱裡因此充斥著雞骨香蕉皮等垃圾,甚不雅觀。更有甚者,有一回,她將要扔掉的老鼠藥也置入冰箱中,我見之大駭。倘惹海倫真合適藝術家這一稱謂,則是世上最粗糙無華的藝術家,非常人眼中附庸風雅之類。
海倫不修邊幅之極端事例發生在第二個月的一天清晨。我打開房門,只見清靜的陽光射進了廚房。又是生趣盎然的一天。海倫的房門緊閉,裡面應該仍是一片夢鄉。我正邁出這一天的第一步,廚房裡的電話機突然鈴聲大作。我正準備走過去接,突然間,海倫房內一陣雜亂聲響,房門驟開,斜刺裡一個披頭散發的海倫衝了出來,和我冷不防打了個照面,我們雙方都震住了。事情可能是這樣的,她近來在等一個重要的電話。當她在被窩裡酣睡時,忽聞鈴聲,就魚躍而起奪門而出。如是以往末有我這個室友之前,她慣於不穿衣服行走。我初搬來,她還處於舊習之中。於是就發生了這樣難堪的一幕:她站在她房門口,下身沒著一物;我站在我房門口,瞠目結舌;我們眼光交錯的一瞬間,彼此都不知道如何收場。本來這無需大驚小怪:大家皆成年人,人終有錯漏之時嘛。可是,接下來的事情卻令我大出意外。她並不尖叫,並不馬上落荒而逃回房間掩面痛哭無臉見人;但見她稍猶豫片刻,即大步流星走去接電話了,仿若無事發生。那五十歲的光屁股,惡惡地晃進我的眼簾,通過大腦再沉入胃部。結果我的早餐難咽,縱使街上的陽光燦爛。事後,海倫也不道歉,我也不好意思開口追究,海倫卻因此得寸進尺。遮羞布一朝褪去,海倫從此無所顧忌,每天晨起皆衣不蔽體,發亂如麻似瘋婦。
從此,我對海倫敬而遠之。

我們住的社區雖窮,倒也整潔,入夜後,社區安寧清靜,無車馬之喧,甚是宜人。海倫煙癮不小,常獨坐門前的小台階上,對著社區街道靜靜地吞飛吐霧,一坐就是半天光景,青銅雕塑的臉紋絲不動。在月光淡淡的夜裡,她端坐著的黑色剪影與周遭混為一體,只有點燃的煙頭的一點紅光晰然可見,還有那四處擴散的白煙,慢慢稀釋入黑夜。我雖刻意避開她,但每每見到這一情景,我又心生同情。門階上坐著,此為休閒;抽煙,亦為休閒。然而,一個中年婦女每夜皆獨自一人如是這般,則不單為休閒,或有戚戚然於心中。她在幽暗處,身體的物理存在被黑夜省略,只剩下思緒,透過煙頭隨著縈繞的煙漫散至夜空。海倫這個硬梆梆之女性,似乎有著綿綿的心緒,煙頭之外她有何內心圖景?
海倫沒有結婚,自二十幾年前離開德國的親人移居加拿大後,就一直單身活著。問其緣由,說:加拿大較德國自由。海淪長於德國鄉下,三鄰四舍皆熟人,多有約束,獨居加拿大,則無人干預其生活決定,且無家室之累,可靜心專功藝術。聼來似爲有理。廚房的冰箱上有張小照片。照片中一位身材高挑勻稱的女孩,在陽光下笑容可掬,頭發上頑皮地插一花朵。一日,我突然喚醒,原來此即海倫之少時模樣。好好一位德國懷春少女,何時淪至不顧顏面的境地?我大爲不解:當初的她,為何不從大衆合大流,不謀正職嫁大婚,反而爲自由故抛離親人故土,偏偏操起男性職業,當公園保安,又偏居一隅做賣不出去的藝術?這自由使她快樂嗎?
彼時的海倫我知之甚少,海倫極少提及,從我朋友處聼來,僅知海倫畢業於德國漢堡大學哲學係,通曉許多理論,曾有中學教職機會,海倫卻不爲所動,毅然投身藝術;現時的海倫朋友不多,她的生活主題似乎只剩下孤獨抑或是單獨。在英文裡“孤獨”(lonely)和“單獨”(alone)是兩不同含義的單詞,初學者容易混淆。前者指心境,後者指處境,比如單獨的人未必一定會感到孤獨;前者被動,後者卻可以是主動,海倫就是主動選擇了單獨;前者是負面的,後者是中性的,甚至可以是正面的,譬如我覺得單獨的旅行很美。然而,對於寄居他國的人,有時候孤獨和單獨這兩種不同的狀態是相互滲透轉換:單獨久了就成了孤獨,適應了孤獨就變回了單獨。五年來,我總是埋頭讀書作畫,尙未有成效,常在孤獨和單獨中徘徊。寂寞難奈時,我會安撫自己說:我不孤獨,因爲我有藝術相伴;我衹是單獨,單獨是藝術家必經之路;縱使是孤獨,亦可激發創作熱情,助我終成大器。門外抽煙的海倫與我不同,她早過了不惑之年,單獨生活的年月漫長,她是否已順應了孤獨,還是更加孤獨?

雖與海倫同一屋檐,我們面聊並不多。她早出早歸,我晚出晚歸,重疊的時間裡彼此各自忙活。每天傍晚我回到家,她大都一個人蝸居在三樓的工作室裡作藝術創作。我會對天花板說一聲“哈羅,我回來啦。”然後樓上就傳來海倫的應聲“你今天過得怎樣?”我機械地對著空氣回答:“很好,你呢?”她又答:“不錯啊。”然後,聞聲不見影的談話就此結束,我走進自己的房間打理自己的畫了。我平常關著房門,以避免見到海倫沒有生氣的青銅臉,影響我藝術創作的心情。當我倆碰巧同時入廚房吃東西,偶爾的面聊才會發生。此時我總是迫不及待地無話找話,促其開口,因爲談話可以緩和海倫的臉色。“你這襪子顏色甚好!”我沒頭沒腦的話,海倫竟信以爲眞,於是面帶悅色,大談此襪子之來龍去脈,視我爲襪子知音。此後,我不敢輕易地讚美她的東西,想到要和她說話就感到泄氣。有時候我想去廚房,但開門前聼到廚房有響聲,我就故意等一會再出去,以錯開與海倫的相遇。
在第三個月的一個晚上,終於有男士來過夜了。海倫自是心情舒暢,喬裝愛清潔地將地板上散落的衣服拾起疊好。男士款款而來,年齡與她相仿,衣著整潔,但話語不多,聽不出是何來頭。夜裡,我隔牆聳耳傾聽,但其房裡並無動靜。翌日,男士早餐後施禮告別,爾後不復光臨。
“你快樂嗎?”有時我也會心生憐憫,關切地問。海倫總是很肯定,稱滿意生活之現狀。話音剛下,下個話題她又恢復了青銅臉,抱怨幾年前有的人譏稱她為納粹。海倫的言語中常含有一股酸酸的嘲諷意味。在談論瑣事上,她常用“有的人”指代某些個她認識的人,並訓斥其不是。在大話題上,海倫也沿用類似之口吻。我們有時談及藝術,海倫總避而不談自己的作品,但愛強調自己藝術理論經綸滿腹。她譏笑加拿大人文理論之教育太少,孰與德國能比。然談及德國之十六世紀文藝復興,海倫又鄙夷德國之淺薄。我未夠博學,不想貿然丈量海倫知識之寬窄深淺。但其態度武斷,世界觀黑白分明,並無學儒之虛谷通達,此為顯見。對於藝術,只有批判,沒有欣賞。對於社會,永遠懷疑,沒有信念。外表強悍的海倫,總故作強勢指摘別人,實爲遮掩自己內心之空虛、藝術事業之失敗。色厲內荏,自欺欺人,又何來快樂?
但有一回她確實是快樂了。第四個月的一天傍晚,她大紅衣服和搖擺裙子地出現在廚房裡,這是我認識她以來首次她換下暗色的衣服。青銅臉一掃而光,她眉飛色舞地對我說,她當晚要赴一藝術圈之舞會,要我品價其裝扮。武打明星著紅衣套綠裙,何來得體?不過,我佯贊其品味,海倫心花努放。道,去年這天,亦此舞會,亦此猩紅墨綠,變化的是披肩和鞋子。她興致勃發地拿出若干皮鞋與我參謀。我不禁啞然:數雙皮鞋羅列,皆高裸、綁帶和低跟,與綠長裙格格不入。我實話相告,勸其買高跟鞋。說話間,門外汽車喇叭響,海倫旋風式地奔下樓去,出門前扭頭給我一句多餘的話——“我走了,有人接我來了,”生怕我不知道。
次日,早餐桌上,海倫寡歡。怨昨晚跳舞太少。我吒異。海倫解釋說,因天不作美,舞會人疏,況且鞋不適腳,總之,客觀理由有若干,使得舞會未能盡興。我半嘲半揄道,待明年此時,你再大紅大紫不遲,何需煩惱?海倫聽罷黯然神傷。可憐的海倫,參與藝術社交證明自己之機會,一年寥寥幾回。每回必成自尊心之重大事件,怎能不患得患失?
和海倫的幾次深談都在聖誕假期前的晚餐桌上。她喜歡靠著牆坐在椅子上,交叉著腿,仰望著廚房昏暗的節能燈。坐定之後,她開始不緊不慢地和我說話,時而露出木納的笑容,時而眼神凝重,時而眼神下垂。她不管做何表情,除手臉之外,身體其餘部位始終保持不動。話到坎子上舒一口氣,談及傷心處,立馬補稱”沒那麼糟“。談話的內容大概如此:她父親已故,母親健在,姐妹有四,皆在德國。有一妹住精神病院,最為掛念。此妹現為癌症晚期,為時不遠。折斷了兩根肋骨達數月之久始被醫生發覺。海倫痛其所痛,眼泛淚花。慨嘆人生離死別之淒惻,未能盡姐妹之恩義守護病榻。我寬慰道,幸而親人皆在,照料有加,爾妹可瞑目而去。海倫長嘆曰,親人皆遺棄此妹,唯吾念之。說畢,長久沉默……
聖誕節後的第三天,海倫終於買了機票,回德國去看望她精神病院裡的癌症妹妹。“再不回去就怕看不到了。”她說。我表示讚許,勸其多呆一段時間。海倫苦言道,薪資低,怕難以為繼,此次飛回去需精打細算。此為海倫的最後一席話,之後我便搬離她家,至今末再聯係。